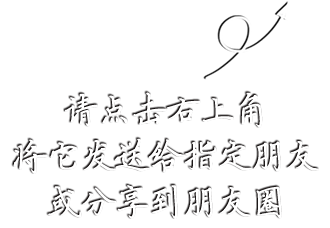北航“月球基地”和月球车。
■本报记者 陈彬
尽管已经临近大四毕业,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吴烈辰还是报了一门叫“星球车技术导论”的校内通识课。用他的话说,“对这门课很感兴趣”。
既然课程是关于“星球车”的,上课的地点就不能仅局限在“地球”上。好在,北航的确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月球基地”,它就在校内一间被改装过的教室里。不大的“基地”被分割成两块,一块的地面上画出了整齐的环形跑道,用以模拟月球基地内部的车辆行驶路线;另一块则遍布微缩版的“环形山”和“月球岩石”。在两块场地上,各有一台月球车静静停在“月球表面”。一幅科幻画铺满整面墙壁。画上,一名宇航员正站在月球上遥望着地球。
“这是我们打造的全国首个面向月球科研基地的数实混合泛在教学平台。”作为“月球基地”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星球车技术导论”课的授课老师,北航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崔勇的语气中满是骄傲。
在这块并不算大的“月球基地”里,崔勇想教给学生什么,吴烈辰又能学到什么?
我们就做月球车
崔勇团队想要建一个“月球基地”的念头最早始于2020年。那一年,我国和俄罗斯确定了一项共同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项目。同年,嫦娥五号任务圆满完成、探月工程三期顺利收官等好消息让崔勇有了一个大胆想法。
“我一直在从事学生的工程实践教学。”崔勇告诉《中国科学报》,在自动化领域,传统的实践教学形式比较单一,往往仅限于学生通过计算机和实验指导书,将课上所学知识进行简单的重复和验证,很难真正发挥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作用。“因此,在实践教学中,我们希望能将‘验证性实验’改为‘竞赛性试验’。”
他解释说:“比如,当我们让学生做一辆小车时,他们‘造车’的过程是否‘按部就班’并不重要,我们评判学生的标准只有一个——谁做的小车跑得最快。”
不过,仅仅“做小车”并不能体现北航作为航空航天特色高校的特点。而此时,接连出现的探月工程好消息让崔勇灵机一动——既然都是“做车”,我们为什么不做一辆“月球车”呢?要知道,北航师生做月球车有着“先天优势”,毕竟我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就是该校未来空天技术学院院长。
有了月球车,建一座“月球基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在崔勇看来,这片颇有些“月球表面”即视感的基地并不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成果,让他骄傲的其实是这片基地背后构建起的一整套数实混合泛在教学平台。
让月球车跑起来
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伴随着对月球车的研发,崔勇和几位老师共同编写了一部名为《星球车混合虚拟仿真技术》的数字教材。然而,当教材编写完成时,出版社却向他们提出了新要求。
所谓“数字教材”,即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传统纸质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转化为适用于各类电子终端的互动性教材。当时,国内不多的数字教材往往只包括音频、视频和知识图谱等内容,很少有数字教材包含虚拟仿真实验,这成为数字教材的明显短板。于是,出版社问崔勇:能不能结合教材内容,开发一套关于月球车的虚拟仿真实验,给其他的教材“打个样儿”?
几经努力,这套适配数字教材的虚拟仿真实验真的被崔勇和同事们设计出来。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数实混合泛在教学平台”。
“我们希望依托这个平台,建立一种‘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人人善学’的数实混合、泛在学习新模式。”崔勇解释说,该平台最大的特点是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具体而言,教师首先从数字教材出发,让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并同步进行在线虚拟仿真实验,“也就是在数字环境中设计一辆属于自己的月球车”。
不过,数字环境总不如实际操作来得真切,而这套系统的一大亮点便是“数实混合”,即学生在数字环境中设计的各种参数以及操作模式,可以直接传输至“月球基地”的实体月球车上,学生可以“实打实”看到月球车按照自己设置的参数运动,这些实际的运行状况又可以为学生优化算法提供一手资料。
此外,该平台之所以被称为“泛在教学平台”,还因为其借助网络的便捷性,使学生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在线访问虚拟仿真实验系统,远距离与“月球基地”的月球车进行互动。事实上,目前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等多所欧洲高校学生已经在远程使用这一平台了。
让实体月球车“跑”起来并不是学生们的学习终点。
在“月球基地”,《中国科学报》记者看到多台3D打印机。崔勇的研究生邓晨晖告诉记者,学有余力的学生在通过计算机设计出自己的月球车后,便可以借助3D打印将月球车“打印”出来,作为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礼物”。在设计、打印与组装的过程中,学生的综合能力再次得到提升。
重构学习空间
在上述实践的基础上,今年春季学期,由崔勇和同事郑建英主讲的全校通识课程“星球车技术导论”正式推出。吴烈辰成为这门课程的首批学生。
目前,这门课程已经结课。回想起在“月球基地”上课的这段经历,吴烈辰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当眼前的月球车按照自己的指令,在“月球表面”翻越“环形山”,以及通过在实体月球车上搭载的激光雷达,扫描出一张周围环境的点云图时的兴奋与激动。
这是崔勇最希望学生获得的感受。
“我们不希望学生按照实验指导书上严格、刻板的步骤,按部就班重复。”他说,自己更希望将“做一台月球车”的目标放在学生面前,引导他们自由想象、学习和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学到的各种知识加以综合运用。
“人工智能、机械结构、控制原理、嵌入式系统……在一台小小的月球车上,可以融合太多知识,这些知识又是学生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崔勇说,“总之,我希望通过这样一台月球车,将学生原本碎片化的知识组合起来。”
受客观条件限制,目前崔勇的“星球车技术导论”课能容纳的学生并不多,但崔勇并不觉得这个“月球基地”只能服务于他的课堂。事实上,他还有着更高的目标。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要重构学习空间,汇聚不同类型的数字化或实体的学习资源,然后重塑学习范式,甚至重塑师生关系。”崔勇说,在这片“基地”,他们的关系不再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画书本”。“我想建立一个开放式课堂,让学生更有兴趣在一起探索。”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对于真实的月球探索自然而然多出了一份向往。
比如,吴烈辰已经保研至航天科工集团,虽然具体的研究方向目前还未确定,但被问及未来是否真的会参与月球车的研制工作时,他笑着说:“为什么不呢?”